9月下旬弟弟從德州打來電話說:「11月初你必需要在香港。」所以我開始了一個為期12天的香港之旅,執行我在生活中做過最艱難的任務之一。
對弟弟的電話我應該回應說——不。但我卻說——好吧!
弟弟不知道的是我在這時需要呆在美國,看著全面的總統大選,但我並沒有告訴他。我想推遲到12月中旬,因為我正在籌備一個380人的2016年《亞裔社區傑出貢獻者》晚宴,會中將表彰前駐華大使駱家輝、眾議員Sharon Tomiko Santos和其他人。
弟弟的提議要提前3個月送媽媽去養老院,我不贊成,因為在精神上我還沒有準備好。我花了2年時間去說服自己,把老媽放在家裡安享她的晚年是對的。因此我沒有多考慮要送她去養老院的種種過程 – 至於該如何開口去告訴她我們的計劃,那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我原來的計劃是在明年2月,也就是農曆新年結束時回香港,在母親入住養老院之前慶祝她的生日。
我知道這次旅行將是沮喪,但有誰能幫助我們做這件難堪的工作,向媽媽解釋她的孩子們要把她送到養老院嗎?這將是對她的「死刑判決」。
十多年前,我已經申請了一張綠卡,讓她留在美國。後來,她放棄了永久居留身份。香港的生活方式更適合她,她說,由於她的文化和語言障礙。我的繼父在2002年去世後,她住在香港有外傭替她打點家事。在香港聘請菲律賓、泰國或印尼女傭是很常見的。
將她送到養老院的緊迫性是因為她得了阿茲海默(A l z h e i m e r)失智症,另一個原因是在家裡缺乏專業護理。雖然醫藥減慢了媽媽疾病的發展,但它不能根治。在過去幾年裡,我們不能在電話上進行5分鐘的談話。過去2年,她開始避免了電話交談,因為她丟掉了好幾次她的助聽器。助聽器不便宜,每隻耳朵的售價是$800美元。她會問同一個問題100次,即使我告訴她20次,卻仍然忘記答案。
媽媽曾經美麗的容顏,如今竟變成了一個雙目空洞的老太太,沉沒的眼睛充滿了恐懼謎惑,有的只是一個生病的心靈;頭腦因失去靈活而扭曲,不能冷靜下來。老朋友們讚揚母親過去模特兒的形象。看到她變形收縮的身體和腳跛不良行的模樣,真令人傷心難過。她可以走路,但是懶得離開輪椅。女傭慣壞了她,大多數時間總把她往輪椅上一放讓她老久呆在那裡。長時間坐在椅子上只會破壞她自己站立的能力。她以前比我高兩英寸,現在,反而是我比她來得高了。
媽媽用盡了她對自己未來安身立命的選擇方法。由於她對財務處理的不小心,使得她在年老之際身無分文。我很遺憾地說,造成這個狀況的部份原因是一些親戚偷竊了她的錢,而有些人知道她沒有錢所以遠離了她。你可能會問,為什麼我不提出她在金錢處理的建議?我不能,因為任何人只要問起她的積蓄都會讓她產生懷疑心。
弟弟和我決定使用支付昂貴公寓和女傭費用的這筆錢,為老媽做遠程計劃,那就是入住養老院。在亞洲把老年人父母送進療養院是恥辱的標記,親戚會援引亞洲的傳統價值觀:是什麼樣的孩子,竟會把老年父母送到療養院?你不是應該照顧他們嗎?你不知道你犯了一個沒有孝道的基本的罪嗎?在被遭到親人反對的風險下,弟弟和我做了適合媽媽的事,弟弟在香港為母親找到了一個不錯的養老院。他也找了家癡呆復健中心讓母親可以每星期四出去參加中心的健腦健身活動。
過渡過程
我們知道,媽媽寧願去死也不願住進集體共住的養老院,所以我們制定了策略來處理她的抵抗。
11月9日,我和丈夫搭乘了一班通宵的航班到達香港,11月11日上午飛機降落在機場。香港比西雅圖時間早16個小時。那天早上當媽媽第一眼看到我時,她欣喜若狂的尖叫、哭泣和鼓掌,像一個小女孩得到她的第一個娃娃似的快樂。

我們靜靜地做各項安排,期間我們從不提「養老院」這三個字,我們要求親戚也這樣做。我們告訴媽媽,房東想要收回公寓,她會搬到一個新的地方。這是真的,因為她的租約於11月14日到期。
整理她東西的感受是相當不愉快的,成堆成桶的東西和堆疊的相冊牽回了我童年的創傷。我們篩揀了她的一些需要用的東西,決定哪些東西是需要丟棄、搬移、存儲或捐贈。她的傢具和電視機都要捐贈,我們告訴女傭只包裝她的基本生活需要,主要是些衣服類。
第一天和最後一天
表兄弟、侄子、女傭、阿姨、丈夫和我共6個人,在11月12日帶她去吃了一頓豪華的點心午餐。午飯後,我們陪她去她的新家。
沒有香檳歡迎媽媽,但更好的是有麻將桌和與其他老人在一起的、被設置為多用途的遊戲間(也用作辦公室和鍛練身體的場地)。媽媽因為脊柱痛已多年不打麻將了,三缺一的朋友也都離她而去。當她像平時一樣坐下來打麻將,你是不會相信她有阿茲海默症的。
之後,一位年輕的社會工作者在她房間面談了她。媽媽喜歡跟英俊的男士談話,她甚至和他一起眉來眼去,調情是沒有年齡限制的,不是嗎!我們從來沒有見過老媽曾有過這麼多的歡笑開懷時刻!

相比本地的華人健安療養院和日本Keiro養老院,她的房間很小(6×8英尺),除了床和電視在牆上,還兩件傢具:一張桌子和一個架子,她的房間裡帶有私人的浴室,價錢並不便宜。療養院每星期一有醫生訪問,護士站就在媽媽的房間外面。每天,社工和護士都會參與老年人的活動項目裡,這就是我們把她搬到養老院,而不是由她自己和印傭生活的原因。媽媽和女傭之間的交流語言通常只限於幾句話:「吃、飽了、要睡覺或上廁所」。
當我去年7月回香港看望她時,她不停地嘆氣:「太安靜,太安靜了!」好的是,她認識到她處在孤獨的環境;壞事是,她不知道如何表達說:「人都到哪裡?我想和大家在一起」。那個瞬間讓我明白,她應該住進養老院。
頭幾天,她只是向我們嘮叨說想回家,「明天」我們只是這樣回答她。第二天,她會忘了她前一天的願望,以前如果她沒有達到願望是會發脾氣,在第二天會做出一些反抗的行為,如拒絕吃飯或吐出食物。

然而這次我們扮演了一個充滿愛心但要求嚴格的父母。我禁止女傭試圖偷偷為老媽帶進來蛋撻和燒烤麵包,因為這是違反養老院的規則。事實是,她最終會在肚子餓了時,不得不妥協去吃下養老院準備的食物,她做到了。療養院提供健康的東西,但不好吃。女傭通常準備好美味,卻是不健康的食物,如油炸蝦和油膩醬油雞。養老院的規矩是只可帶水果給入住的人,凡是含糖和高熱量的食品一概為禁品。
這些日子的每一天,我去養老院兩次。我住在附近的酒店,所以可以在早上和下午晚些時候步行到養老院。除了前兩天,之後的幾天我從來沒有呆著超過1個小時,所以不會產生抑鬱之感。因為在這樣一個與病人、老人和垂死者的環境中,會無形地驅使人產生瘋狂被淹死在那種境況中的陷井中。一個媽媽的鄰居告訴我們,他得了9種不同的病。「我想死」他說,所以我放棄了要丈夫陪我一同去看媽媽的意願,因為的確無需要兩人同時受苦難。
媽媽每次看到我時都快樂地手舞足蹈起來,好像我已經在那裡呆了很久了,她忘了我早上或前一天曾在那裡。她會吻我和擁抱我,她喜歡親吻我和她喜歡的人的手。
每當她說想回家,我會回答:「這裡就是家裡啊!」在過去10來天,我在她的腦子裡加強了很多次這個說法,直到最後一天,我不得不跟她要說再見。
過去每次我告訴她我要離開回美國,她會有情緒反應並掉淚哭泣。雖然我知道在香港的最後一天仍會有這樣的一個場景,但我祈禱希望一個奇蹟。

「媽媽,我明天要走了!」我告訴她。
「去哪裡?」她問。
「要回美國,我會很快回來看你的」我回答。這一次,她的敏感和平靜的反應卻嚇了我一跳。
「你順風吧!」她的答覆居然不是我意料中的。諷刺的是,這回卻換成我泣不成聲。片刻間,她有了清醒的頭腦,運作良好,似乎完全不受不可控的疾病所控制。媽媽認識現實的能力,不是我們這些沒有得病的家庭份子能視為理所當然的。這是我們母女擁抱時,在一起分享產生的美好時刻之一。
我預料這次行程將是艱難、無聊和動盪不安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的確是這樣的,但這也是一個解脫,是對所有那些照顧老年人,隨時被呼喚的工作人員表達著感謝犧牲的獎賞。
同時,我們與女傭的職業介紹所合作終止了她的合同。她照顧媽媽5年了,告訴她我們的決定並不容易,很高興她能理解。我們給她一份退休基金和一個月的寬限期,所以她可以每天去看看媽媽,幫助媽媽調整生活上的改變。我們還確保她找到了一個住的地方,支付她的租金和食宿。
餐飲的樂趣
這段時間讓我的心思能暫時放下的辦法,是通過電子郵件處理即將由西華報主辦的2016年《亞裔社區傑出貢獻者》晚宴。這的確是太棒了,我可以在6,000多英里的遠程距離掌握一些狀況,沒有人知道我人是在香港。
由於我們住在兩個不同的酒店,我們在酒店的地區的北角和太古城(North Point and Tai Koo Shing)附近吃飯。每一餐都是一個盛宴,它給了我們在這個壓力時期期待的東西,大兒子在香港工作,帶我們到一些最有趣的餐館,包括法國和尼泊爾(Nepalese)的餐館。我前高中朋友招待我們各種美食,還包括了私人俱樂部。我怎能否認香港是美食天堂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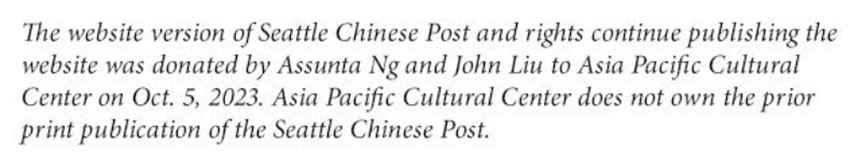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