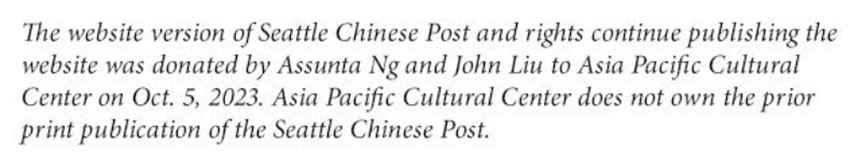靜雯博客
如欲參看英文原文請瀏覽:nwasianweekly.com, under the opinion section
在這個互聯網時代,歷經37年同時經營中英文兩份週報的我來說,是件十分辛苦的工作。我相信我的力量來自修女的教導。
我是在修女村長大的。小學到高中的母校是嘉諾撒聖心書院(Sacred Heart Canossian College-坊間通常叫SHCC或聖心)。書院自1860年以來由義大利修女創立並經營。
我承認, 一些同學對修女們沒有好感。可能是因為她們太嚴格了。不過,這不是我要承認的事。除了其中的一位外,我從沒有感到能親近她們。修女傾向的教育方式不是解釋學生們做錯了什麼,而是強烈地懲罰學生,無情地責罵並引發學生的恐懼。
修女們原本應該與上帝結為連理,心存仁慈。我們這些女學生為什麼有時會惹怒修女們?而同學們所做的一切,有時是不應該被如此對待的。我還記得一位前高中女同學和鄰近學校的男孩們調情後,一位修女摑了她一巴掌。
但在十年前,我對修女過去對待我們的態度產生了變化。這個改變來自與多年來一直無法聯繫的人再次重聚。在參觀了聖心的舊教堂,新建築,下一代聖心和修女之後,我深受感動。一位坐在輪椅上的修女校長年已屆80,過去堅韌的她消失了,取代的是顯露出人性的溫暖。就像一個渴望親情的甜蜜孩子。她要求我們給她一個吻。很高興的是,我們給了她一個吻。
我當時就知道,對一些修女的負面情緒和感覺已悄然消褪。在這樣的時刻裡逐漸讓我意識到,聖心對我人生旅程的影響,我著實對母校有所虧欠。
從那以後,我參加了四次校友團聚,包括聖心成立150週年校慶和最近的多倫多(Toronto)之旅。我以前的幾個同學已經在多倫多定居。他們組織了為期三天的重聚,洋溢著豐盛的晚餐和有趣的節目。修女們是我童年生活和學習的一部份,遺憾的是在重聚時沒有修女出席。但深深地感受到她們在左右。在我們的談話聊天中,經常提到修女們的名字,特別是她們的綽號。那些沒有綽號的修女,可能是被學生們尊敬,或沒有任何特質值得去取綽號。

修女教我們科學,聖經,縫紉和其他科目。我猜想,當學校找不到適任老師的時候,修女就很方便的頂替了。有些修女成了校長,帶領我們走過風暴和榮耀。這些修女們都在不久前去世。我猜想,她們已榮升天堂。
我們女孩經常對修女的生活感到好奇。她們從頭到腳覆蓋的衣裙下,是個什麼樣的生活習慣?她們有長髮還是像尼姑那樣剃光了頭?學生們是不准去她們的住所,那麼她們的生活是什麼樣?兒子從來都不理解為什麼在幾年前,我有興趣看一部關於修女的電影。雖然當時他和我一起去。讀完這篇文章後,我想他會明白的。
無論女孩們喜歡與否,修女都塑造了我們的價值觀。她們的職責是在去世前不過問太多,當然也沒有金錢上的回報。她們教導我們要以無私地,不知疲倦地,去為更大的利益付出代價的理念。在我的職業生涯早期,由於她們的潛移默化,我學會了不是通過捷徑,而是犧牲、努力工作、信念和紀律來要求達到目標。把事情視為理所當然不是我的本性。
堅強的意志力是修女們灌輸給我的。她們的義無反顧,教會了我持續為西華報和英文姐妹報Northwest Asian Weekly奮鬥不懈。讓我們能夠為其他人提供信息,激勵大家並增加力量。即使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但面臨挑戰時卻是無畏無懼。日本諺語說:「因為你,我成就了自己。」我是聖心修女遺產的一部份。為此,我真的很感激。
義大利修女不同於法國修女?
我高三放學後,在法國修女經營的聖保祿修道院的聖母軍(St. Paul‘s Convent‘s Legion of Mary)當義工。每個教會和天主教學校都有自己的軍團計劃,它是一個青年志願者的組織,可以從事慈善工作,包括在醫院探望結核病患者,或探望沒有錢的人在山上蓋的非法小寮屋,或教漁民的孩子們讀書。那些寮屋老早已在香港消失,居民搬到了政府分配的徒置區住房。
聖保祿和聖心都是女子學校。我們並不完全是競爭對手,但聖心的人是具有競爭力。我不想加入我自己學校的軍團。在聖保祿參加課外活動比在聖心更方便,因為離家僅需10分鐘。我的目標不僅僅是為了結識新朋友。而是法國修女比義大利修女更隨和,更有趣。
我從來沒有看到任何法國修女在走廊裡,僅僅是因為學生們的校裙太短而攔下她們。要知道,聖保祿女學生們裙子的長度,在聖心是不可能被接受的。法國修女很喜歡與學生聊天和開玩笑。我從來沒有和任何聖心修女開玩笑。不是我不想,而是對她們太讓我害怕了。一個顯著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們稱聖保祿的修女為姐妹,在聖心稱為母親。母親對孩子的權力是巨大的,而且義大利修女們對學生服從的期望是無與倫比的。
高中畢業後我準備要作個改變,想轉學到聖保祿學院接受我的大學預科教育(在香港叫做Lower Six)。當時,聖保祿的校長和聖母軍的顧問在我還沒有申請入學的情況下,口頭答應錄取我。但是我母親反對,她說:「聖心有什麼不好?」一個享有政府補貼學費的著名學校,是沒有任何問題的。我被一個代表最優秀和最聰明的聖心畢業生主修文科班錄取。這是許多人夢想進去,但被拒錄的班。
然而,我把一切都搞砸了,我想告訴媽媽這些狀況,但缺乏挑戰她的勇氣。在華人和修女的文化中,我們被教育不要與老人和上司爭論,這就是我稱之為「乖女孩」的症狀。我討厭在上下學前坐一小時的公共汽車到聖心,更不用說我必需在單程的路上,轉乘兩趟公共汽車。那年我的心離開聖心,但靈魂卻陷入混亂。我不想再要同樣如我高中時代,只是不斷死讀書和強調考試例程的舊聖心。我需要一個新的環境,來幫助我思考未來想要做的事。我怎麼能有自己人生的腳印?我應該找份工作還是上大學?然而父母並沒有承諾支持我讀大學。我迷茫,孤獨,不安和沮喪。回想起來,我需要的是對未來個人發展方向的諮詢和指導,同時需要有解決問題的喘息機會。但在香港,學校輔導員這個詞是聞所未聞,而老師們忙於承擔巨大的工作量,學生們是很難找到諮詢的。
我母親的反對結束了我對改變的渴望,並為要進的新學校做著美夢。事實上,我為另一位同學創造了一個夢想。她叫馬智文,多年前曾被火燒傷,被聖心拒絕。
遺憾的是,我告訴聖保祿的修女我將無法去她的學校。但她是否願意接受馬智文這位被火災毀容和無指的學生?甚至在沒有見過馬智文的狀況下,修女立即說好。自從我來美國就與馬智文失去了40年的聯繫。
在2009年聖心重聚會上,前同學Rosena Lee說:「你還記得馬智文嗎?」
「我怎麼能不記得?」聽到馬智文的名字,我感到非常高興。
「馬智文告訴我整個故事,說起你是如何幫助她的。」Rosena 說。馬智文和我在2015年重新團聚,她大學畢業後成為一名教師。

馬智文的故事提醒我,她和其他校友的成功故事一樣重要。馬智文可能不如醫生,律師,或銀行家那樣賺很多錢。甚至也不是有香港回歸後的首任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也是聖心校友的陳方安生(Anson Chan)有那樣高調的工作。但她鋼鐵般的生存力,和成功完成學業的意願,令人難以置信和佩服。我們通常是用拇指和四根手指握筆,但她只有兩根指頭。然而她的中國書法寫得相當漂亮。她的樂觀情緒十分具有感染力。

這次重聚的亮點是在最後一次活動中,可真是出人意外。一位前任老師Vivian黃出席了晚宴。她是教我們英國文學的老師,在多倫多退休。雖然身材嬌小,但79歲的她仍然看起來挺精神的。在我們這個時代,她是少數沒有醜聞的教師之一。她很受尊敬,也是很多學生最喜歡的老師,包括我已故的同學Diana Wong。「我是Assunta Ng(吳靜雯)。」我上前打招呼。「我可不可以有您的講詞?」我問黃老師。她說:「我曾教過兩個Assuntas,一個是Assunta Ng,另一個是Assumpta Koo。」她在教過的成百上千的學生中,居然還記得我!這不僅令我驚喜,而且深慰我心。因為我在班上只不過是個平庸的學生而已。
房間裡有痛苦和歡樂。幾位同學過世了。有些同學的配偶剛剛去世。淚水在同學的臉頰流淌。房間裡佔主導地位的主要是笑語歡聲以及許多手機的點擊。聖心是一所女子學校,但仍然有15位男士與我們共聚。這是因為通過婚姻,他們成為了聖心的鐵粉絲。
當我們彼此告別時,我們期待畢業後50年在香港舉行的大團聚。我相信有些修女會共襄盛舉。但她們不會是那些教育過我們的人,她們也不會是義大利人。自1997年中國從英國接收香港以來,現在聖心的面孔都是些年輕的和大多數是華人的修女了。
我期待著再見到大家…。因為見到她們,我會特別感謝修女們,在培育下一代成為傑出女領袖所付出的大愛和無私的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