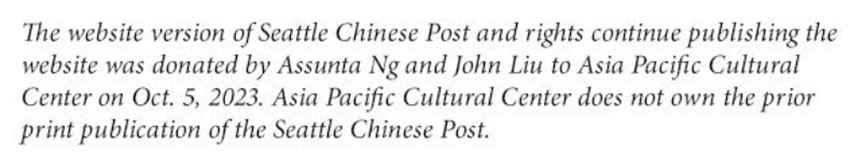公元1931年初夏,母親出生在四川巴縣觀音岩。我外婆家本是當地富戶,但因其父母早逝,由兄長做主將她嫁給了常年外出幫工的外公。盡管外公每年臘月才回家團圓,但絲毫沒有影響生兒育女。外婆一輩子生下了10個孩子,有3個夭折,還剩姐弟7人,大姨媽為長,母親次之,還有5個舅舅。我的大哥與么舅同年出生,在那個年代,母女同時坐月子屢見不鮮。
7歲那年,母親隨全家徒步搬遷至黔北沙土鎮,當街是外公新開的《楊家藥舖》,後院是居家場所。母親性格像男孩,開朗、倔強、好動,平時喜愛唱歌、游泳、打籃球。在那沒有髮乳、髮油、髮膠的年代,母親總要拿點菜油或者清水把頭髮打濕,梳理得清清爽爽,才會出門。無論在哪兒讀書,母親都是「校花」級的人物。
在中國新舊政權更替那年,解放大軍分兵多路向南方進發,但地處邊陲的西南大地依然保持著舊時的風貌。陰曆冬月初十,母親在爺爺創辦的「普惠學校」,經由一場西式集體婚禮嫁入王家,在家鄉被傳為「才子配佳人」的神話。
結婚前一年,母親從貴陽回來度暑假,在閨蜜的婚禮上充當伴娘,以天仙般知識少女的形像驚艷全場。在貴大法律系上學的父親王榮江,未見其人,就夢想要「抱得美人歸」,請慈善的爺爺派人去提親,被外公一口回絕,說自己是外來戶,今後落葉要歸根,不願將女兒嫁入此地,永遠流落他鄉。
與此同時,沙土鎮上吳姓大戶仗著與政界要戶車家的甥舅關係,要娶楊家女兒做二房。1930年代末,車家大小姐車儀留學東洋歸來,嫁給了時任國軍第94軍軍長的牟廷芳,更使車家在周遭威名大振,無人敢惹。吳家托鎮上第一媒婆攜重金聘禮前來,外公不卑不亢,使其掃興而歸。然而,吳家變本加厲,竟提著槍,公開揚言要上門搶親。
楊家見勢不妙,讓母親四處躲藏。一天清晨,在同學家過夜的母親剛起床,就聽見敲門聲,嚇得又躲進了裡屋。同學開門打探,原來是自己的二哥。母親沒有想到此二哥就是那位託人求過親的王家二公子,更沒有想到自己的這位閨蜜王榮英,竟與這位少爺是同父異母兄妹。就這樣,兩人相識,父親說,母親聽,有言來卻少有語往。但無論如何,兩人開始熟悉起來。
爺爺在鎮上的二房冉氏奶奶是個文化人,住著前後三排進深的大院,屋裡不但存放著祖上幾百年間留傳下來的各類讀物,還保留著現代三位叔伯爺爺和
大伯讀大學帶回來的書籍。住在鎮郊甘溪河的王家孩子經常來這裡小住幾日,一邊享受集鎮生活,一邊好好讀讀書。小學三年級的暑假,父親在這裡埋頭苦讀古典四大名著,在經過《三國、水滸和西游》以後,實在上不去「婆婆媽媽」的《紅樓》,回到甘溪河,被爺爺教訓了一通。
1984年的春天,我家先生正在川大讀研,為做課題,來貴州幾家軍工企業聯繫使用計算機。我倆一起去了遵義南北鎮,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榮英孃孃。我們一起生活了三天,在她開設的羊肉粉館裡享受了最美味的羊雜碎米粉,最香醇的鴨溪窖酒和最甜蜜的人間親情。
有天晚飯後,孃孃告訴我們,父母偶遇的第二天,她就帶著《西廂記》一書去見母親,說那是父親推薦給她讀的。其實,那書中夾帶著父親在貴大拍攝的標準照和抄寫在照片背面的一首唐詩,
曾經滄海難為水 除卻巫山不是雲
取次花叢懶回顧 半緣修道半緣君
以此告訴母親,他對所有的花都不屑一顧,現在就賴上你了;又過一天,王家媒人再次登門,雙方訂親,然而最打動楊家的話語無疑是「在沙土地界,如果與王家聯姻,誰還敢前來搶親?」
母親原名楊大勻,是父親給她改名為楊淑潔,取賢淑而又純潔之意。可後來一起在貴陽讀書交往不久,父親就發現母親「潔」有餘而「淑」不足,好似舊時深宮閨秀,根本不懂談情說愛。每當他倆在一起,母親的行為總是古怪,往往令人尷尬,百分之百的「男女授受不親」。
有一次,父親請母親和幾位好友一起到貴大做客。進屋後,母親害羞,既不敢與父親肩並肩、更不敢與他面對面,而是騎在長板凳上獨自面壁而坐,令幾位青年忍俊不住。又有一次,父親到貴陽女中約會母親。門房進去叫人,母親出來,一見父親,調頭就走,把父親一人丟在那裡犯傻。還有一次,父親來訪,已到母親住的樓上,母親竟衝出來,把父親一把推下樓去,差點兒摔上一大跤。父親所說的「淑不足」,除了這些所說不懂如何表達愛意外,還在說她具有鬥爭性,得理不饒人。在家鄉黔西工作幾十年,不論你是哪級領導,局長、縣長或書記,她都敢當眾頂撞,且大多取得勝利。
其實,母親有許多優點,「潔」當然是優中之優。家裡平時的雜事大多有大孃操持,但母親總抽空把家裡擺弄得整整齊齊、乾乾淨淨,有時還會親自採一束鮮花,插在茶杯裡,裝點客廳。無論搬家何處,我們王家的整潔是人所共知的。
父母成姻看似一樁美滿姻緣從天而降,母親為了躲避邪惡勢力,嫁入王家,以求平安,但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整個社會很快就顛倒了。在土改封門前夜,母親背著未滿週歲的大哥,懷揣私下得到的區政府路條,逃至貴陽,與父親會合,躲過了一場可能的滅頂之災。然而,王家這把保護傘從此卻成了全家頭上的緊箍,而唐僧隨時隨地可以念動咒語。
初到黔西縣城的父母,一個在學校,一個在銀行,拼命工作,努力改造,日夜操勞,常常吃住在單位,甚至雙方有半年時間不能見面,以期從剝削階級家庭原罪中解放出來。那時母親剛滿二十,明目皓齒,一條粗黑的長辮常常甩在胸前,依然一副清純少女的形像,自然引來一些南下西進領導的青睞。在種種誘惑下,飽受政治高壓的母親面對再次「逃亡」的可能,心中糾結,難以訴說。是一步重新登天,還是堅守婚約?被父親稱為「淑不足」的母親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