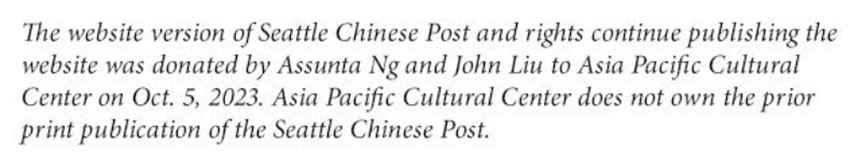在COVID期間,這是一條艱難的路,他在紐約疫情大流行期間,將他的手術室轉變為COVID重症監護室。但是現在,雷景恆(Philip Louie)博士回到他的家鄉華盛頓,為當地社區提供脊椎護理。
雷景恆是父母從香港和澳門移民到美國的孩子,他對骨科和脊柱外科手術很早就產生了興趣。
「我與一個一直強調幫助我們周圍的人的家庭和社區一起成長……隨著年齡的增長,醫學尤其是外科手術領域令人興奮,因為它為我提供了機會來幫助我周圍的人。我喜歡修復斷裂的骨骼,肌肉,韌帶,肌腱以及脊椎的所有奇妙解剖結構……我的父母都患有持續不斷的背椎問題,並成功進行了脊柱手術。我的祖父母因關節炎和脊柱側彎而遭受了數年的背痛,而且我也得到了極大的祝福,那就是也能幫助他們。」。
雷景恆長大後從父母和祖父母那裡汲取脊椎和背痛教訓,並將其應用於自己的生活中。
「家庭和社區是我成長的基石。 實際上,這些是如此重要,以至於許多社區成員都感覺彼此像家庭成員!…在這個當今充滿分裂和充滿緊張氣氛的環境和世界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的是要了解造成我們分裂的原因並記住我們可以成為(並且是)一個大家庭。」
他學到的另一個教訓是克服差距。
「我們所有人都為某事而苦苦掙扎,而我們中的許多人都為許多事情而苦苦掙扎。隨著生活中一切的進行,很容易讓這些鬥爭成為我們的桎塞……作為脊椎外科醫師,我經常面對處理與自己差異懸殊的人,無論是由於疼痛,無力,壓力還是不確定性造成的。我有幸有機會與我的患者作為一個團隊面對這些差異領域,並為他們提供許多有愛心的醫療團隊成員的廣泛支持。」
雷景恆在華州和全美範圍內都看到了這些鬥爭。由於去年紐約發生的大量COVID病例,他成為醫護人員的一部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COVID疫震中的中心當然很有趣。感覺就像是這一天,這座城市還活著,在跳躍,但第二天,燈光熄滅了……人們生病了,到處都是喪命的病患……作為脊柱外科醫師,發生的事情遠遠超出了我的舒適範圍。 但是我學會了,我的角色是支持我的醫療同事和社會。」
雷景恆的父母一直是亞裔美國人社區的定期活動家。
「我的父母是開拓者, 他們在塔科馬(Tacoma)建立了the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華人社區中心,Evergreen Chinese Academy常青中文學院,International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 f Tacoma塔可馬華人基督教會,Ruston Christian Childcare a nd Preschool Ruston育兒中心。我父親開始了自己的醫學實踐。每一步,我們都面臨公開種族主義和攻擊的形式,看著我的父母站起來並直接與之抗爭是一件非常獨特的事情。他們非常活躍於社區事務。」
雷景恆的父母沒有屈服於這些挑戰,而是將其視為一個積極的機會。
「他們從中找到了很多快樂。我認為他們喜歡這些類型的障礙……從這個角度來看,暴力行為的增加繼續困擾著我們的AAPI社區,這凸顯了我們當前面臨的緊張局勢。這是毀滅性的和令人悲傷的!但是,我們必需學會站起來,成為社區的力量,譴責這些行徑並教育我們的兄弟姐妹。」
雷景恆現在回到華州,並與位於西雅圖第9大道的弗吉尼亞梅森方濟各會健康(VMFH)神經科學研究所合作,以及在Federal Way剛剛開業的VMFH脊椎診所工作,雷景恆終於有機會一直在等待讓本地患者成為他大家庭的一部份。
「那意味著我將帶領病患們了解他們所關心的一切,並讓病人們知道我在想什麼,為什麼我有這個想法……我問自己,如果病人是我的家庭成員,我會推薦些什麼樣的治療方案?」
 雷景恆看到了一種趨勢,只有大流行的不安全感加劇了這種情況,使病人(尤其是年老的病人)進院找他看病。他發現,這種趨勢在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AAPI)患者中更為明顯。
雷景恆看到了一種趨勢,只有大流行的不安全感加劇了這種情況,使病人(尤其是年老的病人)進院找他看病。他發現,這種趨勢在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AAPI)患者中更為明顯。
「患者告訴我,他們多年來只是一直忍受著脊椎痛苦,麻木,刺痛和無力,因為他們不知道該向誰求助,卻從未得知要注意哪些常見症狀,沒有足夠的資源來尋求醫療救助,也不了解為什麼脊柱,脊髓以及這些伸展到胳膊和腿的神經如此重要,需要長期保健,還有無數其他狀況!」
特別是AAPI病人希望尋求AAPI的照顧者,並希望能帶家人去尋求支持,由於安全預防措施,在COVID期間很難做到這一點。
「西華盛頓州擁有龐大而多樣的AAPI社區,但是,在我們採用大型多學科脊柱計劃治療的患者中,他們所佔的比例非常低。在為他們的使脊柱衰弱相關的問題尋求護理時,我經歷了他們的恐懼和不確定性。」
據雷景恆說,如果儘早發現,許多脊柱問題不需要手術,但這與許多人的看法相反。
「那是很多人感到害怕的地方。他們不知道從哪裡開始。在Virginia Mason Franciscan Health,我們有幾位AAPI脊柱外科醫生……以及非脊柱專家。他們經過培訓可以幫助病患解決脊椎問題,他們不是外科醫生,但他們想方設法不讓病人作手術。」
雷景恆笑著承認,如果患者最初去看他的一位同事,「如果早點接受治療,他們甚至可能根本不需要見我。」